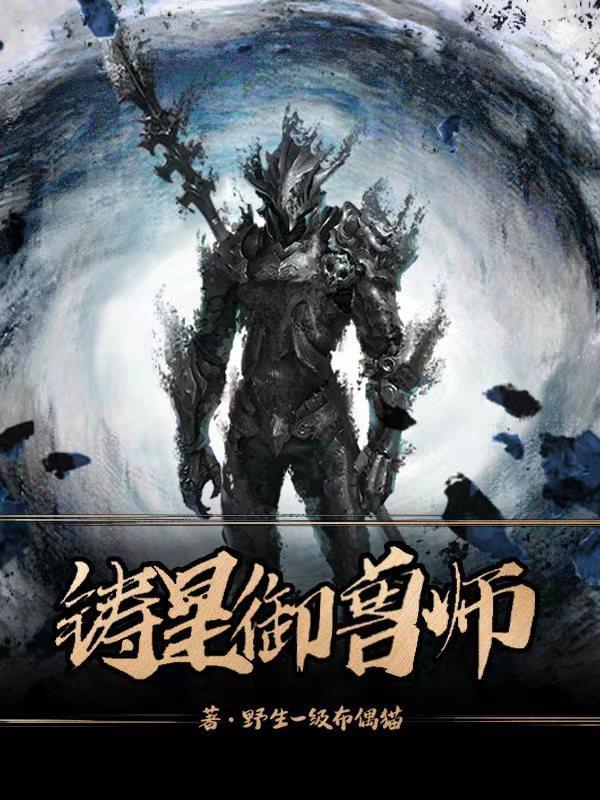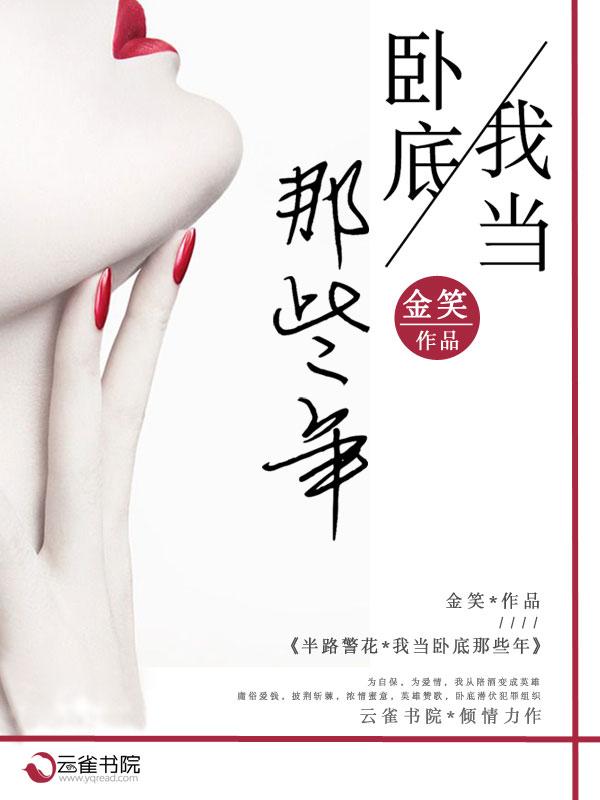630看书网>饮马山川 > 第26章 剑断雪落(第1页)
第26章 剑断雪落(第1页)
粗糙的羊皮纸信封,带着风沙和远方萧瑟的气息,静静躺在冰冷的黑铁案几上。送信人,一个裹在灰扑扑斗篷里的瘦小汉子,面如死灰,连呼吸都轻得几乎断绝。他不敢看古星河的眼睛,只是深深垂着头,将身子缩成一团,仿佛想把自己嵌进冰冷的石板地里。他双手捧着一个更小、更陈旧的纸包,上面残留着一点早已干涸发暗、宛如泪痕的痕迹。
“将军……长……长公主让……让送来的……”汉子声音抖得不成样子,每一个字都像从齿缝里艰难地挤出来,“是……是雪柠姑娘……最后……最后……”
“最后”两个字终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,他膝盖一软,重重跪倒,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,肩膀剧烈地抽动,压抑的呜咽在空旷冰冷的军机堂内闷闷地回荡。
案几后的身影,像一尊早已凝固的玄铁雕像。古星河的手指搭在冰冷的桌沿,指节因用力而泛出青白色。他的目光越过跪伏在地的信使,死死钉在那小小的纸包上。那上面的暗红,像一根烧红的针,狠狠刺进他眼底深处。镇北城凛冽的风,透过厚重的石窗缝隙钻进来,带着塞外特有的、能割裂皮肤的寒意,吹动了他额前几缕散落的黑发,也卷起那羊皮信封的一角,发出沙沙的轻响,如同鬼魂的低语。
死寂。整个军机堂只剩下那压抑的呜咽和窗外呜咽的风声。
许久,久到地上的人几乎以为自己要在这无边的死寂中窒息。一只骨节分明、带着薄茧的手,缓缓伸了过去。动作很慢,仿佛每一个关节都在承受着千钧之重,带着一种近乎凝固的迟滞。指尖触碰到那小小的纸包时,冰凉的触感瞬间传遍全身。
他拿起它,很轻。轻得像一片羽毛,却又重得让他几乎拿不稳。
他挥了挥手,动作疲惫而僵硬。跪着的汉子如蒙大赦,几乎是连滚爬爬地退了出去,沉重的木门在他身后合拢,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响。偌大的军机堂彻底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。
古星河低下头,看着手中的纸包。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里面折叠的纸张边缘。他小心地拆开外面一层早已失去韧性的粗糙纸张,里面是一封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笺,用的是宫中才有的细腻云纹笺。信笺下,压着几页更小的、边缘毛糙的纸片,像是从什么簿子上匆匆撕下来的。
他先展开了那封信。熟悉的、娟秀又带着点倔强棱角的字迹,瞬间灼痛了他的眼睛。
“哥,当你看到这信的时候,雪柠大概已经走啦。”开篇第一句,就带着一种残忍的平静。
“别难过,也别生气。哥,真的,我其实……没那么害怕了。就是……就是有点想你。想镇北城的风,想城墙上被夕阳烤得暖暖的石头,想阿骨烤的硬邦邦的饼,想红绡姐姐给我梳头时笨手笨脚的样子……还想你板着脸,却又偷偷给我塞糖的样子。”
字迹在这里停顿了一下,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,仿佛一滴凝固的泪。
“哥,天启城很大,很漂亮,金灿灿的,晃得人眼睛疼。可这里一点都不好玩。冷,骨头缝里都冷。他们……都不喜欢我。他们看我的眼神,像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破烂玩意儿。”
“有个很凶的嬷嬷,总骂我。她说我是‘野种’,说我们镇北城的人都是‘不服王化的蛮子’。哥,我知道我不是野种!你是天下最厉害的人!你是鬼谷先生的弟子!你是守住镇北城的英雄!我……我只是……想回家……”
“哥,他们打我的时候,我就数窗外的梧桐叶子。一片,两片……数着数着,好像就没那么疼了。数到一百片,我就偷偷在心里喊一声‘哥’。好像……好像你就在外面看着我一样……”
信笺在古星河手中开始难以抑制地颤抖。那娟秀的字迹仿佛化作了滚烫的烙铁,每一个笔画都在灼烧他的掌心,烧穿他的皮肉,一直烫进骨髓深处。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而艰难,每一次吸气都像在吞咽带刺的冰渣,每一次呼气都带着胸腔深处沉闷的、濒死的回音。一股腥甜的铁锈味在喉咙深处弥漫开来,又被他死死地压了下去。他死死咬着牙关,下颚绷紧的线条锐利得像要割裂空气。鬼谷传人的傲骨,镇北城主的威仪,此刻都成了囚禁滔天巨浪的脆弱堤坝。
他颤抖着,拿起那几页撕下来的小纸片。上面的字迹更加潦草、稚嫩,甚至有些歪歪扭扭,是更早些时候的零星记录。
“11月23日阴。手指好痛,嬷嬷说我顶嘴,用戒尺打的。哥,我不怕疼,但她说哥哥是反贼,是朝廷的敌人……我咬了她一口!被她关在柴房了。柴房好黑,有老鼠跑过去的声音。哥,我不怕黑,就是……有点冷。”
“12月11日雨。窗外的梧桐叶被打掉了好多。那个穿黄衣服的坏蛋又来了,他看我的眼神……像曲红绡姐姐说的,山里的饿狼。他摸我的脸,我吐了他口水。他又打我了……嬷嬷也在旁边骂。哥,我记住他的脸了!等我出去了,一定要学哥哥的剑法!打回去!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“12月20日雪。好大的雪啊,白茫茫的,盖住了天启城。他们说我病了,不给我炭火。我裹着薄被子,看着窗外的雪。哥,镇北城的雪更大吧?你守城的时候,是不是也这么冷?我偷偷藏了一小块你给我的糖,一直没舍得吃。舔了一下,真甜……好像没那么冷了。”
纸片上的字迹越来越凌乱,笔划虚弱地颤抖着,仿佛书写者已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。其中一页的顶端,被撕扯得参差不齐,边缘还沾着几抹刺目的、早已干涸发黑的血渍。那血痕,像一把生锈的钝刀,反复割锯着古星河早已麻木的神经。
他的目光死死锁在信笺的最后几行。那字迹不再是娟秀,而是扭曲、虚浮,每一个笔画都透着濒死的挣扎和深入骨髓的恐惧:
“……哥,他们来了……好多人……他们把我按在地上……用……用白绫……勒得好疼……喘不过气……骨头……骨头要断了……哥……我不哭……你说过……镇北军的骨头……是……是硬的……我……没……丢你的脸……”
“……哥……我想……回家……”
“回家”两个字,写得尤其用力,却又被一大片模糊、深褐色的水迹彻底洇开、晕染,几乎不成字形。那晕开的痕迹边缘,还沾着几粒极其细微、凝固的深色颗粒。
古星河的身体猛地一颤!他死死盯着那片洇开的“回家”,仿佛第一次看清那是什么——那不是水痕,是血!是她的血!是她在窒息濒死时,从咬破的嘴唇、从勒紧的喉咙里涌出的血泪!那几粒凝固的深色颗粒……是血块!
轰——!
那根名为理智的弦,彻底崩断了。
堤坝在无声的咆哮中彻底崩溃。一股滚烫的、带着浓重铁锈腥气的液体猛地冲上喉头,再也无法压制。“噗!”一口炽热的鲜血狂喷而出,星星点点,溅落在信笺上,溅落在“回家”那模糊而绝望的字迹上。滚烫的血珠与早已干涸冰冷的血泪痕迹瞬间交融、渗透,不分彼此。
他高大的身躯剧烈地摇晃了一下,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脊梁。他下意识地用那只握过无数强敌咽喉、挥动过令天下胆寒长剑的手,死死撑住了沉重的黑铁案几。冰冷的铁质触感丝毫无法平息体内那足以焚毁一切的业火。
没有嚎啕,没有嘶吼。只有一种压抑到极致、仿佛从灵魂最深处被撕裂开来的呜咽。那声音破碎、沙哑,不成调子,如同濒死的野兽在喉管被割断前最后的挣扎。泪水,滚烫的、混着鲜血的泪水,终于决堤。不是清澈的溪流,而是粘稠的、赤红的血泪!它们争先恐后地涌出眼眶,沿着他刚硬如石刻的脸颊,混合着嘴角不断溢出的鲜血,大颗大颗地砸落。
一滴,一滴,沉重地砸在信纸上,砸在那片被血泪和鲜血反复浸透的“回家”二字上。
就在那滚烫血泪砸落的瞬间,诡异而骇人的一幕发生了。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男团出道的我演戏爆火了 地府来个火阎王 天生甜宠命3[快穿] 偷渡余生爱你 论如何拯救路人甲师尊 她在贵族学院发疯[双周目] 欢迎来到唯我至上主义教室 纯人类保护手册[星际] 和离后怀了仙尊的崽 王者对弈 如何杀死龙傲天宿敌 花痴,但忍界最强 带崽离婚回家继承亿万家产 这个咒灵操使有点意思 梦里看见昨天 在仙山里种田养猪 快穿之忠犬攻略计划 死神再就业指南 分手后前男友成了顶流 仙道败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