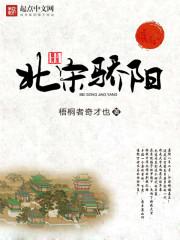630看书网>大秦之我是杀手 > 第1267集 江南的养蚕(第1页)
第1267集 江南的养蚕(第1页)
吴郡茧事
第一章雨笠载愁来:楚地的五月,麦浪刚翻完最后一波金浪,蚕房里的新茧就缀满了竹匾,白得像堆在檐下的雪。李婶正蹲在蚕房里捡茧,指尖刚触到一颗饱满的茧子,就听见院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混着江南口音的呼喊:“李婶!李婶在家吗?”
她擦了擦手上的蚕沙,掀开门帘出去,就见一个穿青布短衫的女子站在院心,裤脚沾着泥点,手里提着个半旧的竹蚕筐——筐底破了个小洞,残留着几片发黑的桑叶,还有一只蜷缩的病蚕尸体,看得人心里发沉。
“你是?”李婶迎上去,见女子眼眶红得像浸了水的樱桃,手里还攥着块皱巴巴的织锦,锦面上的花纹只织了一半,丝线断得七零八落。
“俺是江南吴郡的阿绣,”女子声音发颤,把织锦递过来,“俺们郡里靠织锦过日子,家家户户都养蚕。可这两个月,蚕不知咋了,先是拉白便,后来浑身发僵,一天能死一筐。俺们照着楚地传的法子,给蚕房通风、晒桑叶,可没用——吴郡的雨下起来就不停,蚕房里潮得能拧出水,桑叶刚摘下来就沾着露水,晒半天也晒不透。”
阿绣说着,把空蚕筐举起来,指着眼眶:“这筐子,前儿还装满了三龄蚕,今早就空了。俺男人去外地收丝,家里就靠俺织锦换粮,再这么下去,俺们村的织坊都要关了……”
李婶接过蚕筐,指尖触到筐壁,还能感觉到残留的潮气。她想起三年前楚地闹蚕病,也是死了大半蚕,最后是她和过世的丈夫琢磨着用干稻草铺底、炭火烘蚕房才稳住。可吴郡的潮湿,比楚地的梅雨季还厉害,老法子定然不管用。
“你别急,”李婶转身回屋,翻出个蓝布包袱,里面装着两包蚕种——一包是楚地选育的“楚肥蚕”,抗病性强;另一包是去年和西域商队换的“西域丝蚕”,吐的丝更粗亮。她又把丈夫留下的养蚕笔记揣进怀里,笔记里记着这些年遇到的蚕病和应对法子,纸页边缘都被翻得发毛。
“俺跟你去吴郡,”李婶把包袱挎在肩上,又拿起墙角的竹编雨笠,“路上俺再想想辙,吴郡潮湿,关键是要给蚕房去潮气,还得让桑叶不沾露。”
阿绣没想到李婶这么痛快,眼泪一下子涌出来,拉着她的手连连道谢。两人当天就跟着去吴郡的商队启程,船行在江南的水道上,两岸的芦苇荡绿得发沉,雨丝像牛毛似的飘着,落在船板上,很快积起一层水。
李婶坐在船舱里,翻开养蚕笔记,手指在“蚕病诱因”那页划过:“蚕喜燥恶湿,湿度过高则蚕体虚弱,易染白僵病”。她抬头看向窗外,见岸边的竹子长得郁郁葱葱,突然眼睛一亮——吴郡多竹,竹篾透气又防潮,若是用竹篾铺蚕房,说不定能解潮气的问题。
她赶紧在笔记上画了个竹篾的图样,又写:“竹篾铺底,间距半指,可通风去湿;桑叶需晨露干后采摘,晒至半干(叶片发脆但不卷边),再喂蚕”。阿绣凑过来看,指着图样:“俺们村后山就有竹林,编竹篾的匠人也多,要是这法子管用,俺们现在就能准备。”
李婶点点头,把笔记合上:“到了吴郡,先去看看你们的蚕房,再定具体的法子。”船行得慢,雨却越下越大,李婶望着舱外的雨雾,心里默默盼着,能赶在吴郡的蚕全死光前,把法子想透。
第二章湿屋困蚕魂
船行五日,终于到了吴郡的码头。刚下船,潮气就裹着水汽扑面而来,比船上还厉害,李婶的蓝布包袱刚放在地上,没多久就沾了一层细水珠。
阿绣的村子在吴郡东南,叫蚕娘村,村里几十户人家,几乎都围着织坊转。刚走到村口,就见几个妇人坐在织坊门口抹眼泪,织机上的经线松松垮垮,旁边的蚕筐里,零星躺着几只病蚕,身子已经发僵。
“阿绣,你可回来了!”一个穿灰布衫的妇人迎上来,见了李婶,眼里闪过一丝希望,“这就是楚地来的李婶?”
“是俺,”李婶走到织坊旁边的蚕房,推开门,一股霉味混着潮气扑面而来。蚕房是土坯墙,屋顶盖着茅草,地面是夯实的泥土,踩上去软软的,能感觉到地下的潮气往上冒。几排木架上摆着竹匾,匾里的蚕大多蔫蔫的,有的趴在桑叶上不动,有的已经蜷缩成一团,桑叶上还沾着细小的白便。
“俺们天天开窗通风,可雨下得勤,开窗就淋雨,关窗又潮,”阿绣指着墙角,“你看,墙根都长霉了,竹匾里的桑叶放一天就发黑。”
李婶蹲下来,摸了摸竹匾的底,果然潮乎乎的。她又拿起一片桑叶,指尖能感觉到残留的露水,叶子边缘已经开始发黄。这时,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拄着拐杖走进来,看了李婶一眼,语气带着点质疑:“你就是来教俺们养蚕的?俺养了四十年蚕,吴郡的潮气,不是靠通风就能去的。前儿俺们试着用炭火烘蚕房,结果把蚕烘得脱水,死得更快。”
阿绣赶紧介绍:“王伯,这是李婶,楚地的蚕病就是她治好的。”
王伯哼了一声,指着竹匾里的蚕:“楚地干燥,跟吴郡不一样。俺们吴郡养蚕,历来是用稻草铺底,虽说潮点,可也没像今年这么邪乎。”
李婶没反驳,而是走到屋外,绕着蚕房转了一圈。蚕房背靠山坡,坡上的雨水顺着墙根往下流,地面没有排水的沟,雨水都渗进了土里,难怪蚕房里这么潮。她又看向村后的竹林,青竹长得笔直,叶片上挂着水珠,在雨雾里透着生机。
“王伯,俺们先试三天,”李婶转身进屋,“你让村里的匠人编竹篾,要宽半指、长两尺的,编成交叉的篾垫;再让村民摘桑叶时,等太阳出来,露水干了再摘,摘回来放在竹筛里,架在炭火上烘——不是用大火烘,是用余温,烘到桑叶不沾手、叶片发脆就行。”
王伯皱着眉:“竹篾比稻草滑,蚕能站稳吗?炭火烘桑叶,会不会把叶子里的汁水烘没了?”
“竹篾编成交叉纹,缝隙不大,蚕能站稳,而且透气,潮气能从篾缝里散出去,”李婶拿起一片桑叶,“桑叶半干的时候,汁水还在,只是没了露水的潮气,蚕吃了不容易闹肚子。俺们楚地也试过用竹篾,只是楚地干燥,用得少,可吴郡多竹,正好能用。”
阿绣见王伯还在犹豫,赶紧说:“王伯,俺们都快没蚕了,不如试试李婶的法子,总比坐着等强。”
王伯叹了口气,拄着拐杖往外走:“行,俺让村里的匠人编竹篾,要是不管用,可别怨俺们没提醒你。”
当天下午,村里的匠人就砍了竹子,在晒谷场上编竹篾。李婶也没闲着,跟着一起编,教他们把竹篾编得疏密适中,既透气又能托住蚕。阿绣带着几个妇人去摘桑叶,等太阳出来,露水散了才动手,摘回来的桑叶放在竹筛里,架在灶台上,用做饭后的炭火余温烘着。
李婶坐在灶边,不时翻一下桑叶,指尖试着重度:“烘到这样就行,不能太干,不然蚕吃着费劲。”
阿绣学着她的样子翻桑叶,看着桑叶慢慢变得干爽,眼里有了点光:“俺以前总怕桑叶晒坏,没想到烘一下反而好。”
“吴郡的潮气大,就得顺着潮气来,”李婶笑着说,“不是跟潮气硬拼,是想办法把潮气引走。”
第三章竹篾初显灵
三天后,第一批竹篾垫编好了。李婶带着村民把蚕房里的旧竹匾清空,把竹篾垫铺在竹匾底部,再铺上一层薄桑叶——这次的桑叶是烘过的,叶片干爽,没有露水,闻着还有股淡淡的清香。
村民们把剩下的蚕小心翼翼地移到新竹匾里,阿绣捧着一只病恹恹的小蚕,手都在抖:“这是俺家最后几只三龄蚕,可别再死了。”
李婶帮她把蚕放在竹篾垫上,蚕刚落上去,先是愣了一下,接着就爬到桑叶上,慢慢啃了起来。阿绣眼睛一亮:“它吃了!以前放新桑叶,它们都懒得动。”
王伯站在旁边,也凑过来看,见蚕真的开始吃桑叶,眉头皱得松了点。李婶又把蚕房的窗户调整了方向,朝东南开,避开西北来的雨水,还在墙根挖了条浅沟,把山坡流下来的雨水引到村外的水沟里。
“蚕房里的潮气,一半是外面渗进来的,一半是桑叶和蚕的呼吸带来的,”李婶指着竹篾垫,“竹篾透气,潮气能从底下散出去,再加上窗户通风,沟里排水,潮气就留不住了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,李婶每天都守在蚕房里,观察蚕的状态。第一天,蚕拉的白便少了;第二天,没有新的蚕发僵;第三天,蚕开始蜕皮,进入四龄期,身子比以前壮实了不少。
阿绣早上进蚕房,见竹匾里的蚕都在动,桑叶被啃得坑坑洼洼,高兴得直拍手:“李婶,你看!蚕蜕皮了,比以前胖了一圈!”
王伯也来了,蹲在竹匾边,摸了摸竹篾垫,还是干爽的,再摸以前的木架,也没有以前那么潮了。他拿起一只蚕,放在手心,蚕在他手心里爬动,力气比以前大了不少。
“没想到这竹篾还真管用,”王伯语气软了下来,“俺以前总觉得老法子好,看来是俺固执了。”
李婶笑着说:“老法子有老法子的好,可遇到新问题,就得改改。吴郡的竹多,用竹篾既方便又省钱,比从楚地运稻草来强。”
可没过几天,又出了新问题。那天夜里,突然下了场暴雨,风把蚕房的窗户吹开了,雨水灌进蚕房,淋湿了两匾蚕。阿绣早上发现时,蚕都缩在竹篾垫上,浑身湿漉漉的,有的已经不动了。
“这可咋整?”阿绣急得哭了,“刚好转点,又出这事。”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娱乐:我小鲜肉,开局杨老板带娃堵门! 兽世生存与爱 顶级Beta,被AO倒认妻主 午夜围炉茶话会 重生88,带着三个哥分家致富 和高冷学姐不认识,但孩子8岁了 娇欲恶雌忙捡夫,全员疯批争求宠 傅先生,偷偷领个证 天道无私情 名柯观影体:论犯人的多样性 诡异深空:我的小破船无限升级 穿成男频文里的极品炉鼎(修仙np) 高甜来袭,莲花楼里的两个剑神 凌仙战纪:医道燃血破九域 人在末世,收容异常 我是你们白月光?不是绿茶男二吗 夜半惊情,霸道妖夫太黏人 霍格沃茨的日常系玩家 诡异末世降临,开局我就加入基地 快把这王位拿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