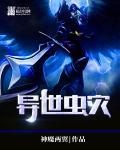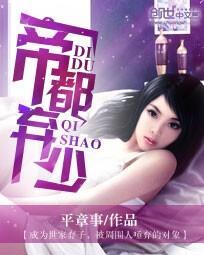630看书网>青史为证河山即名什么意思 > 第204章 麦浪验丰岁仓廪藏新方(第1页)
第204章 麦浪验丰岁仓廪藏新方(第1页)
芒种的日头刚爬过老桑树顶,共耕田的麦浪已泛着琥珀色的光。饱满的麦穗把秸秆压成弧形,穗尖垂落的姿态竟如列国农夫弯腰劳作的剪影。秦国汉子腰间别着竹制的“验丰尺”,尺身刻着“穗长三寸为丰,二寸为歉”的刻度;楚国农妇篮里装着青铜“辨种镜”,镜面打磨得能照见麦粒纹路;鲁国田夫推着改良的“风扬车”,车斗里新添了分级筛网——这些昨日刚赶制的新家伙,正等着给今年的收成定个虚实。
老桑树下的“华夏”剑鞘上,去年的“育苗纹”已被新长出的“验穗纹”覆盖。公孙矩展开赵氏家族传下的《辨麦七法》竹简,泛黄的竹片上赵无恤亲笔批注:“麦之丰歉,非独在量,更在质。穗满而粒瘪,终是虚收。”他用指尖轻叩竹简上“穗、粒、色、质、重、味、藏”七个朱字:“今年咱们不仅要收得多,更要收得好,这七字验麦法可得记牢了。”
王二愣子刚割倒的麦捆还冒着热气,他抓起麦穗在验丰尺上一比,正好齐着三寸刻度线:“公孙先生您看!这穗长够数,就是颗粒松紧不一,有得穗子饱满,有的却发瘪。”说话间孟春提着陶甑走来,甑里飘出草木灰的清香——按她祖母传下的古法,用槐叶灰水浸泡新麦可辨优劣,饱满麦粒会沉底,空瘪的则浮在水面。小石头蹲在田埂边,正用辨种镜细看麦粒:“这颗麦壳上有虫眼!俺得挑出来!”
一、验麦新法的巧较量
验麦工具刚在晒场摆开,列国农夫就起了争执。秦国的张大哥把验丰尺往麦堆里一插:“按咱秦地规矩,穗长过三寸就算好麦!”楚国的刘婶却举着辨种镜反驳:“光长没用!你看这麦粒有黄斑,定是遭了夜露,藏不住的。”鲁国的王大叔干脆转动风扬车摇柄,车斗里的麦粒立刻分出轻重两堆:“空瘪的被风吹走,留下的才是真收成。”
“都别急着争。”公孙矩让人取来五国麦穗各一束,分别插在陶盆里,“赵无恤当年在晋阳验麦,用的是‘五感法’。”他先让众人闭眼摸麦穗:“秦国麦穗粗硬,楚国麦秆柔韧,这是水土之别。”再让小石头咬破麦粒:“鲁麦微甜,燕麦带涩,味不同则藏法各异。”最后教大伙用验丰尺量穗长、用称麦斗称千粒重,五种方法试过,原本各执一词的农夫们都露出了信服的神色。
秦国竹匠正在修改验丰尺,在三寸刻度下又加了“粒距半分”的细痕:“穗长够了还不行,麦粒间距得匀,不然容易掉粒。”他给尺尾装了小秤砣,“现在既能量长短,又能称轻重,一杆两用。”楚国农妇们则把辨种镜镶在木框上,框边刻上对比图谱:“这是饱满粒,这是虫蛀粒,一看就明白。”
最热闹的要数改良风扬车。王大叔给车斗加了三层筛网,上层滤秸秆,中层分大小粒,下层接麦糠:“往年扬三遍才干净,现在一遍就成。”他往车里倒了半斗混着碎壳的麦粒,摇动手柄,清麦落进底仓,碎壳从侧槽飞出,引得围观者连声叫好。
二、跨族验麦的真学问
验麦开始后,列国农夫自发结成五组,每组都有秦、楚、鲁三国人。秦国汉子负责量穗长称重量,楚国农妇专司辨色挑虫粒,鲁国田夫掌管风扬分级,配合得竟比种麦时还默契。王二愣子组刚验完东头半亩地,竹牌上已记满数据:“穗长三寸二,千粒重六钱,虫蛀率不到一成,这收成顶呱呱!”
公孙矩沿着晒场巡查,见孟春正教秦国姑娘用槐叶灰水验麦:“浮着的这些得单独晒,不能入粮仓。”又看到小石头帮鲁国大叔摇风扬车,踮着脚够把手的样子让人心疼,便给他做了个垫脚木凳:“验麦要细心,更要省力。”李掌柜提着新蒸的麦饼走来,饼香混着麦糠味飘满晒场:“验麦累了,垫垫肚子再干!”
验到西头地块时出了岔子。楚国农妇发现这里的麦粒普遍偏瘦,风扬后轻粒占了三成。“这地块去年种的豆,怎么麦质反倒差了?”刘婶犯了嘀咕。公孙矩翻开《辨麦七法》,指着“轮作需补肥”那条:“豆类吸地力,种麦前得施草木灰。看来今年秋耕要记着这事。”他让大伙把瘦麦单独存放:“这种麦做麦麸最好,磨面反而费功夫。”
夕阳西斜时,验麦结果汇总到公孙矩手中。竹简上密密麻麻记着:共耕田亩产比去年增两成,其中中上品麦占七成,虫蛀霉变率不足三成。“按赵无恤的标准,这是‘上丰’年成!”公孙矩把竹简举得高高的,晒场上顿时爆发出欢呼声。小石头举着他挑出的最大麦粒跑来:“师父你看!这颗能当种子不?”
三、突遇霉变的巧应对
正当大伙准备分装粮食时,刘婶突然惊呼:“南头几捆麦发霉了!”众人赶过去一看,果然见麦穗上长了白霉,原来是昨日雨后没及时翻晒。“这可咋办?扔了可惜,留着怕坏了好粮!”王二愣子急得直搓手。
公孙矩却不慌不忙:“赵无恤在竹简里写了‘霉变急救法’。”他立刻分派人手:秦国汉子负责把霉麦挑出来摊开暴晒,楚国农妇取来干艾草铺在底下吸潮,鲁国田夫烧起无烟火堆熏杀霉菌。“记住要离地二尺晾晒,让风从底下过。”他边示范边讲解,“霉斑轻的还能做饲料,重的只能当燃料,绝不能入仓。”
张大哥发现霉麦多在捆心,恍然大悟:“定是收割时捆得太实,潮气散不出去。”他当即把验丰尺改了用途,用尺尾的铁钩挑松麦捆:“以后收麦得留透气缝,宁慢三分,不霉一粒。”孟春则找来干谷壳,垫在霉麦底下:“祖母说谷壳吸潮,比艾草还管用。”
忙活至深夜,霉变麦总算处理妥当。王大叔蹲在火堆旁烤霉麦,忽然眼前一亮:“这烤焦的麦粉能做记号!”他用麦粉在粮仓门上画了防潮符:“既除霉味,又好记验麦日期。”小石头也学着在自己的储麦罐上画小记号,歪歪扭扭的样子引得众人发笑。
四、仓廪藏新的大学问
处理完霉变麦,储粮准备正式开始。鲁国的王大叔带着人给粮仓做最后检查,在仓底铺了三层防潮物:最下层是晒干的芦苇,中间铺草木灰,上层盖油纸:“这样保管三年不发霉。”秦国的张大哥则在仓壁上划刻度,每尺标上日期:“按月查粮,少了多少一眼便知。”
楚国农妇们的工作最细致。她们把验好的麦按品级分装,上品麦用陶罐密封,中品麦装麻袋,下品麦编草囤存放。刘婶教大伙在罐口盖松针:“松针防潮还驱虫,比麻布强。”孟春则把公孙矩批注的储粮口诀抄在布上:“干、净、隔、透、查,五字记牢不犯傻。”
公孙矩特别关注种子粮的储藏。他让小石头把挑出的饱满麦粒倒进陶瓮,每装一层就铺层干沙:“沙藏麦种来年出芽齐。”又在瓮口糊泥密封,只留个透气小孔:“既防鼠又保气,这是赵无恤的‘瓮藏法’。”史官路过见了,在《春秋会要》续卷里写道:“赵氏藏麦之法,虽隔千年,用之仍效,所谓古法新用,莫过于此。”
阿柴在粮仓周围撒了圈苍术粉,这是他从山里学的土办法:“这药粉驱虫,比硫磺好闻。”李掌柜则带来新做的粮票,竹片刻着“壹斗”“伍升”字样:“凭票领粮,免得乱拿。”小石头也想要粮票,公孙矩便给他做了个迷你版:“等你学会验麦,就给你正式粮票。”
五、验丰宴上的新感悟
收仓完毕,杂院摆起“验丰宴”。桌上的菜都带着麦香:麦仁粥、麦粉糕、麦秆熏肉,连酒都是新酿的麦酒。王二愣子端起酒碗:“今年收得多,更收得明白!这验麦的法子得传下去。”刘婶给大伙分麦粉糕:“明年咱把辨种镜再改改,让小姑娘也能学会。”
公孙矩把《辨麦七法》竹简传给众人传阅:“赵无恤说‘验麦如验人,表里需如一’。种地不光要下力气,更要懂门道。”他给每人发了块竹牌,上面刻着各自负责的验麦任务:“来年咱们分组竞赛,看谁验得准、藏得好。”
小石头最兴奋,他得到了公孙矩亲手做的小验丰尺。“俺明年要学全套验麦法!”他举着尺给大伙看,尺尾还刻着个小麦穗。小黄狗叼来块麦饼,蹲在他脚边摇尾巴,像是也在庆祝丰收。月光透过老桑树洒下来,照在剑鞘新长的“藏丰纹”上,泛起温润的光。
六、岁月沉淀的丰岁道
芒种后半月,粮仓上的藤蔓已爬满仓顶。列国农夫常来查看粮食,按公孙矩教的方法每月翻晒一次。秦国汉子发现麦堆下沉,立刻补填新麦;楚国农妇闻到潮气,马上开窗通风;鲁国田夫检修风扬车,为下次扬粮做准备。
王二愣子把验麦数据刻在石碑上,立在老桑树下:“让后人知道咱今年的收成多实在。”小石头则把验麦工具画下来,贴在杂院墙上:“等俺老了,就教娃娃们认这些家伙。”有个老农夫感慨:“种了一辈子地,今年才明白,好收成是种出来的,更是验出来的。”
公孙矩擦拭着“华夏”剑,剑鞘上的纹路又多了几重。从育苗到收割,从验麦到储藏,农耕的智慧就像这层层纹路,刻进木头里,也刻进人心间。他望着仓廪前忙碌的身影,忽然明白:所谓丰收,不只是仓廪充盈,更是把每粒粮食都看得金贵的心意。
风吹过粮仓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像是在数着仓里的麦粒。有人说这是粮食在生长,有人说这是古法在低语。只有公孙矩知道,这是千万双手共同书写的农耕史诗,每一粒粮食都在诉说:丰岁从来不是偶然,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必然。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论绿茶攻是如何上位的? 苏家风云录:四杰逆天行 ASI超级个体之宇宙心流 恶毒美人又被教训了 孤掌 缺爱小少爷的专属Daddy 第七子,血字遗诏 古穿今之可爱小厨娘的腹黑影帝 凤凰玦 归瑕 秦宫绮梦:幼师穿越之皇后养成记 死对头双双失忆后 洗白我是专业的[快穿] 师尊不许我成亲 卿卿入我怀 京阙雪 天痕:玉佩中的时空囚徒 重生71年带空间,嫁糙汉 穿成恶雌,五个兽夫跪求我别走 硝烟淬骨劫红颜,涅盘真火铸圣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