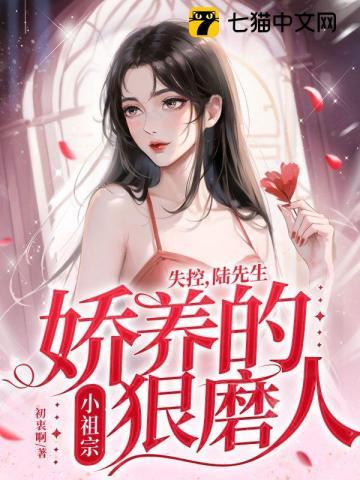630看书网>历史的回响300字 > 第243章 处下居上 孔子言行里的处世智慧(第1页)
第243章 处下居上 孔子言行里的处世智慧(第1页)
孔子于乡党,恂恂如也,似不能言者;其在宗庙朝廷,便便言,唯谨尔。
仲秋的午后,我在古籍馆翻阅《论语?乡党》,读到“孔子于乡党,恂恂如也,似不能言者;其在宗庙朝廷,便便言,唯谨尔”时,眼前忽然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:在鲁国的乡邻间,孔子温和恭顺,仿佛不善言辞;而在祭祀的宗庙、议事的朝廷上,他却言辞流畅,只是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态度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行姿态,跨越两千多年的时光,依然清晰地勾勒出一位智者在不同场合的处世之道——在乡党间放低姿态,以谦逊融入社群;在朝堂上明晰表达,以责任践行使命。
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,礼崩乐坏却又礼乐尚存,乡党是宗族伦理的重要载体,宗庙朝廷是国家礼制的核心场所,不同场合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规范与言行要求。孔子的言行差异,并非虚伪的“两面性”,而是对场合伦理的深刻理解与尊重:在乡党,需以“讷”显恭谨,维系邻里间的和谐;在朝堂,需以“辩”明事理,承担治国理政的责任。这种“处下则讷,居上则辩”的智慧,不仅是孔子个人修养的体现,更成为了后世中国人待人接物、履职尽责的重要准则。
从孔门弟子对老师的记载,到后世文人学者对“场合伦理”的践行,再到现代社会人们在生活与工作中的言行选择,孔子的这份处世智慧始终在传承。它不是对个性的压抑,而是对秩序的尊重;不是对责任的逃避,而是对使命的担当。接下来,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孔子的“乡党”与“朝堂”,探寻他言行差异背后的处世哲学,感受这份穿越时空的智慧力量。
一、乡党之“讷”:谦逊恭顺的处世姿态
“孔子于乡党,恂恂如也,似不能言者”,这里的“恂恂”,是温和、恭顺的样子;“似不能言者”,并非真的不善言辞,而是刻意收敛锋芒,以谦逊的姿态融入乡党社群。在古代社会,乡党是由宗族、邻里构成的小型共同体,维系其稳定的核心是伦理亲情与礼仪恭让。孔子在乡党间的“讷”,正是对这种社群伦理的尊重与践行——不张扬、不炫耀,以温和恭顺的言行,守护邻里间的和谐氛围。
(一)“讷”之内涵:放低姿态,融入社群
乡党间的“讷”,首先是一种“放低姿态”的自觉。孔子虽学识渊博、声望卓着,却从不以“智者”“贤者”自居,在乡邻面前,他始终将自己置于“平等一员”的位置,用温和恭顺的言行消除身份差异带来的距离感。《论语?乡党》中还记载:“朝,与下大夫言,侃侃如也;与上大夫言,訚訚如也。君在,踧踖如也,与与如也。”即便在朝堂上与不同等级的官员交谈,孔子也会根据对方的身份调整言行姿态,更何况在更为亲近的乡党间。
在春秋时期的乡党社群中,“年长有序”“尊卑有别”是重要的伦理规范,但这种规范并非冰冷的等级压迫,而是以亲情为基础的和谐秩序。孔子的“恂恂如也”,正是对这种秩序的维护——面对长辈,他恭敬倾听,不随意打断;面对同辈,他温和交流,不争执强辩;面对晚辈,他耐心引导,不居高临下。这种放低姿态的言行,让他与乡邻之间没有隔阂,真正融入到社群生活中。
比如,每逢乡党间的祭祀活动或婚丧嫁娶,孔子都会积极参与,并且严格遵守礼仪规范。在祭祀时,他会按照辈分依次行礼,不越矩、不张扬;在宴席上,他会主动为长辈布菜,倾听长辈讲述宗族往事;在邻里遇到困难时,他会尽己所能提供帮助,却从不求回报。乡邻们提起孔子,都说他“温和可亲,如同自家兄长”,这种评价,正是对他乡党之“讷”的最好认可。
孔子的“讷”,不是怯懦,也不是虚伪,而是一种“共情式”的处世智慧——他深知,乡党社群的和谐,需要每个人放下身段,以真诚与恭顺对待他人;只有融入社群,才能真正理解百姓的生活,才能让自己的学说贴近现实。这种放低姿态的“讷”,为他后来“仁者爱人”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等思想的形成,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。
(二)“讷”之价值:化解隔阂,守护和谐
乡党间的“讷”,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化解隔阂,守护社群的和谐。在乡党这样的小型共同体中,人与人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,难免会有利益摩擦或观念分歧,而“温和恭顺”的言行,正是化解这些矛盾的最好方式。孔子的“似不能言者”,并非真的沉默寡言,而是在非原则问题上不争执、不辩解,用包容与理解化解分歧,维护社群的整体和谐。
《孔子家语》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:孔子在乡党居住时,邻居家的孩子与自己的弟子曾参发生了争执,原因是两人对一句古诗的理解不同。孩子的父亲得知后,觉得很不好意思,特意上门向孔子道歉。孔子却笑着说:“古诗的理解本就没有唯一答案,孩子们各有见解是好事,何必道歉呢?”随后,他还特意邀请邻居父子到家中做客,让曾参与邻居的孩子一起探讨古诗,两人不仅化解了矛盾,还成为了好朋友。
在这个故事中,孔子没有因为曾参是自己的弟子而偏袒他,也没有用自己的学识去“纠正”邻居孩子的观点,而是以温和的态度包容不同意见,用沟通的方式化解隔阂。这种“讷”的言行,不仅让两个孩子重归于好,更维护了邻里间的和谐关系。正如孔子所说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在乡党间,真正的君子,是在保持自身原则的前提下,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,用温和的言行守护社群的和谐。
在现代社会,乡党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共同体,但社区、邻里依然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场所。孔子乡党之“讷”的智慧,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价值。比如,在社区生活中,难免会遇到邻里间的小摩擦——楼上孩子吵闹影响楼下休息,邻居占用公共空间堆放杂物,等等。此时,若能像孔子那样,以温和恭顺的态度与对方沟通,不指责、不抱怨,往往能更好地化解矛盾;反之,若态度强硬、言辞激烈,只会激化矛盾,破坏社区和谐。
孔子的乡党之“讷”,告诉我们:在日常生活的社群中,“争理”不如“共情”,“辩解”不如“包容”;放低姿态,以温和恭顺的言行对待他人,才能真正化解隔阂,守护和谐的生活氛围。
(三)“讷”之修养:克己复礼,内化于心
孔子乡党之“讷”,并非刻意伪装的言行,而是“克己复礼”修养的自然流露。“克己复礼”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,指的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与个性,遵守礼仪规范。在乡党间,“礼”的核心是“恭顺”“谦和”,孔子的“恂恂如也”,正是将这种礼仪规范内化为自身修养的结果。
孔子一生都在践行“克己复礼”的修养。他曾说:“吾日三省吾身: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这种自我反省,让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,使其符合礼仪规范。在乡党间,他会反省自己是否对长辈足够恭敬,是否对邻里足够友善,是否在言行上有张扬之处;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,他将“恭顺”“谦和”的礼仪内化为自身的本能,最终形成了“恂恂如也,似不能言者”的言行姿态。
这种“内化于心”的修养,让孔子的乡党之“讷”没有丝毫做作之感,而是充满了真诚。比如,当乡邻向他请教问题时,他不会因为对方学识浅薄而轻视,而是耐心倾听,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;当乡邻对他的学说提出质疑时,他不会急于辩解,而是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,若对方言之有理,便会虚心接受。这种真诚的“讷”,让他在乡党间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与信任。
在现代社会,“克己复礼”的修养依然重要。它不是要求我们压抑个性,而是要我们在社群生活中,克制自己的傲慢与偏见,尊重他人、包容他人;将“谦和”“恭顺”的美德内化为自身修养,用真诚的言行对待身边的人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像孔子那样,真正融入社群,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。
二、朝堂之“辩”:明晰严谨的言说智慧
“其在宗庙朝廷,便便言,唯谨尔”,这里的“便便言”,是言辞流畅、条理清晰的样子;“唯谨尔”,是指虽然言辞流畅,但始终保持严谨、谨慎的态度。宗庙是国家祭祀祖先的场所,朝廷是国家议事决策的地方,这两个场合都与国家礼制、治国理政息息相关,需要清晰、准确的言说,才能确保礼仪的规范与决策的正确。孔子在朝堂上的“辩”,正是对这种场合需求的回应——以流畅的言辞阐明观点,以严谨的态度坚守原则,承担起治国理政的责任。
(一)“辩”之必要:明晰事理,履职尽责
在宗庙朝廷上,“辩”是履职尽责的必要条件。宗庙祭祀关乎国家礼制的传承,每一个环节、每一句祝词都有严格的规范,若言说模糊不清,很容易违背礼仪;朝廷议事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,每一项决策、每一个观点都需要清晰的论证,若言说混乱无序,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。孔子作为熟悉礼制、心怀天下的学者,在宗庙朝廷上必须“便便言”,才能明晰事理,履行自己的责任。
比如,在宗庙祭祀时,孔子会根据祭祀的对象、规模,清晰地阐明祭祀的礼仪流程、祝词内容以及每个环节的象征意义。他会向参与祭祀的官员解释“为何要祭祀”“如何祭祀”“祭祀的意义是什么”,确保每个人都能理解并遵守礼仪规范,避免出现失礼的行为。在朝廷议事时,孔子会针对国家面临的问题,如赋税改革、军事防御、外交政策等,清晰地提出自己的观点,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进行论证。他的言说条理清晰、论据充分,让官员们能够准确理解他的主张,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。
《论语?先进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,孔子回答:“政者,正也。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随后,他又详细阐述了“为政以德”的观点,认为统治者只要自身品行端正,以身作则,百姓自然会效仿,国家就能治理好。他的言说条理清晰,既点明了治国的核心,又给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法,让季康子深受启发。这个故事,正是孔子朝堂之“辩”的生动体现——以清晰的言辞阐明治国之道,履行自己作为学者的责任。
孔子的朝堂之“辩”,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,也不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认可,而是为了明晰事理,帮助国家做出正确的决策,守护百姓的福祉。这种以“履职尽责”为目的的“辩”,让他的言说充满了责任感与使命感。
(二)“辩”之准则:严谨审慎,坚守原则
孔子的朝堂之“辩”,虽然言辞流畅,但始终以“严谨审慎”为准则,坚守自己的原则。在宗庙朝廷上,言说不仅关乎个人形象,更关乎国家礼制与百姓利益,因此必须严谨对待,不能有丝毫马虎;同时,言说也必须坚守“礼”“义”的原则,不能为了迎合他人而违背自己的信念。
在宗庙祭祀时,孔子的“严谨”体现在对礼仪细节的严格把控上。他会仔细核对祭祀的器具、祭品是否符合规范,祝词的用词是否准确恰当,参与祭祀的人员的站位是否符合辈分。若发现有不符合礼仪的地方,他会及时指出并纠正,哪怕对方是地位尊贵的诸侯或大夫。他认为,宗庙祭祀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一丝一毫的疏忽都可能违背祖先的意愿,损害国家的福祉,因此必须严谨审慎。
在朝廷议事时,孔子的“严谨”体现在对观点的充分论证与对原则的坚守上。他提出的每一个主张,都会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进行详细论证,不主观臆断,不夸大其词;同时,他也会坚守“礼”“义”的原则,若自己的主张与国家利益、百姓福祉相违背,他会及时调整;若他人的观点违背了“礼”“义”,他会据理力争,不妥协、不退让。
比如,当鲁国的大夫季氏想要祭祀泰山时,孔子坚决反对。因为根据周礼,只有周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泰山,季氏作为大夫,祭祀泰山是“僭越礼制”的行为。孔子找到季氏的家臣冉有,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:“祭祀泰山是诸侯的礼仪,季氏作为大夫,没有资格祭祀泰山。若他执意为之,便是违背礼制,会遭到上天的惩罚。”虽然冉有未能阻止季氏,但孔子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,用严谨的言说阐明了“礼”的重要性。
孔子的朝堂之“辩”,告诉我们:在关乎责任与原则的场合,言说不仅要清晰流畅,更要严谨审慎、坚守原则;只有这样,才能确保自己的言行符合道义,才能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责任。
(三)“辩”之智慧:因人而异,因事而变
孔子的朝堂之“辩”,还蕴含着“因人而异,因事而变”的智慧。在宗庙朝廷上,面对不同身份的人(如君主、诸侯、大夫)、不同性质的事(如祭祀礼仪、军事决策、民生问题),孔子会调整自己的言说方式与内容,以确保对方能够理解并接受自己的观点。
面对君主时,孔子的言说会更加委婉、恭敬,既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,又不冒犯君主的权威。比如,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,孔子回答:“文武之政,布在方策。其人存,则其政举;其人亡,则其政息。”他没有直接指责当时的政治弊端,而是通过引用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治国经验,委婉地向鲁哀公提出“为政在人”的观点,让鲁哀公能够虚心接受。
面对诸侯或大夫时,孔子的言说会更加直接、具体,结合实际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。比如,卫国大夫孔圉问孔子如何处理政事,孔子回答:“先有司,赦小过,举贤才。”他直接指出了处理政事的三个关键:明确官员的职责、赦免小的过错、选拔贤能的人才,让孔圉能够直接应用到实际政事中。
面对不同性质的事情时,孔子的言说重点也会有所不同。在讨论祭祀礼仪时,他会重点强调礼仪的规范与象征意义;在讨论军事决策时,他会重点强调“仁政”的重要性,反对穷兵黩武;在讨论民生问题时,他会重点强调“富民”“教民”,提出具体的赋税、教育政策。
这种“因人而异,因事而变”的言说智慧,让孔子的朝堂之“辩”既清晰有力,又富有弹性,能够适应不同的场合需求,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。在现代社会,这种智慧依然具有重要价值。比如,在工作中,面对不同的沟通对象(如领导、同事、客户)、不同的工作任务(如汇报工作、讨论方案、解决问题),我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言说方式与内容,才能更好地达成沟通目标,完成工作任务。
三、内外之衡:孔子言行背后的处世哲学
孔子在乡党间的“讷”与在朝堂上的“辩”,看似矛盾,实则是他“内外之衡”处世哲学的一体两面。“内”是私人化的社群生活,核心是“和”,需要以谦逊恭顺的“讷”维护和谐;“外”是公共性的政治场合,核心是“责”,需要以清晰严谨的“辩”履行责任。这种“因场合而异”的言行选择,不是对自我的割裂,而是对“礼”的深刻理解与对“道”的坚定践行——在不同场合选择合适的言行,既是对他人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责任的担当。
(一)“礼”为准则:言行随场合而变的根基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陷入爱 炮灰小师姐重生后,麻溜离开宗门 费土旧士 妻子残害亲女儿,只为讨好白月光 不良人:殿下收手吧!前方玄武门 海疆共明月 重生之母盼女福 异能觉醒天命星辰 食光记 都重生了谁还恋爱脑! 我拒绝嫁给校草 娇养美强惨祖宗后,咸鱼被迫卷赢 重生:找将军当靠山 穿越1960 陆子的王朝逆袭之旅 阵云高:英雄寂寞 风吹骨响 洪荒之人掌天地 半世浮沉一世梦 政道问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