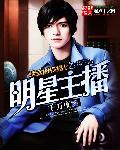630看书网>太平广记白话故事在线听 > 第78章 方士三(第2页)
第78章 方士三(第2页)
第二天,众人准时赴约。王琼打开瓷罐,一股浓郁的桂花香扑面而来——罐子里的桂花不仅全开了,花瓣还比昨天更饱满,连颜色都鲜亮了许多,仿佛刚从枝头摘下来一般。有人忍不住伸手摸了摸,花瓣柔软湿润,绝不是假花。
这下,没人再敢说王琼是江湖骗子了。有人问他这法术是怎么学的,王琼却只是笑着说:“哪有什么法术?不过是懂些草木生灵的习性,再加上一点耐心罢了。”
后来,有人说王琼其实是个精通生物学的奇人,知道如何用特殊的方法让龟卵快速孵化,也懂如何调节温度和湿度,让花朵在密封的罐子里绽放。不管真相如何,王琼的戏法总能给人带来惊喜,也让人们明白:这世上许多看似“神奇”的事,背后不过是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和对事物的深刻了解。
就像那片瓦变龟、枯花重开,看似违背常理,实则藏着对自然规律的精准把握。生活中的许多“不可能”,往往不是真的做不到,而是我们缺少发现规律的眼睛和坚持下去的耐心。只要肯用心,平凡的日子里,也能开出意想不到的花。
4、王固
唐宪宗元和年间,襄州城里最风光的官,要数节度使于崸。这人办事雷厉风行,性子却急得像燃着的炮仗,见不得半点拖沓。那日他正在府里处理公文,门吏来报,说有位叫王固的山人求见。
于崸摆摆手让进来,没等多久,就见个老者迈着缓步进了厅堂。王固穿件洗得发灰的粗布道袍,须发半白,躬身下拜时,动作慢了几拍——原是他膝盖有些不便,起身时还扶了扶桌角。于崸本就没耐心,见他这模样,心里先矮看了三分,问话时语气也淡淡的:“先生来此,有何见教?”
王固倒不在意,只说自己云游四方,听闻于公爱结交奇人,特来拜会,还想献上一手绝活。可于崸见他谈吐寻常,衣着朴素,只当是来混饭吃的江湖客,敷衍了几句便让门吏送他出去,连留饭都没提。
过了几日,于崸在府里设游宴,请的都是襄州的官员和名士,席间吹拉弹唱,好不热闹。王固在驿馆里听说了,心里难免不是滋味——他本是真心来投,却连个赴宴的机会都没有。思来想去,他想起前几日去使院办事时,见过判官曾叔政,那人待人温和,倒不像于崸那般急躁。
于是王固寻到曾叔政的住处。曾叔政见他来,忙起身迎客,还亲手倒了杯热茶。王固接过茶,叹了口气:“我原以为于公是惜才之人,才不远千里赶来,如今看来,是我错了。不过蒙判官您厚待,我走之前,给您露一手,也算不负这番礼遇。”
曾叔政听得好奇,忙点头应下。王固从怀里摸出两样东西:一节拇指粗的竹管,两头塞着木塞;还有个比铜钱还小的小鼓,鼓槌细得像根棉线。他先打开竹管的木塞,又折了根细树枝当鼓槌,轻轻敲了敲小鼓,“咚、咚”两声,清清脆脆。
没等曾叔政反应过来,竹管里“簌簌”响了起来——几十只指甲盖大的蝇虎子爬了出来,黑亮亮的壳,细腿上还带着浅黄的绒毛,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,落在桌案上。王固又敲了三下鼓,蝇虎子“唰”地分成两队,像两军对垒似的,一队朝东,一队朝西,站得笔直。
接下来的场面,让曾叔政惊得眼睛都瞪圆了。王固的鼓点时快时慢,敲三下,蝇虎子就变“天衡阵”,前后两排交错,像架着盾牌的士兵;敲五下,又变“鱼丽阵”,小虫子们三三两两依偎,像水里的鱼群;再敲几下,还能排成“鹤列阵”,一列列斜着站,翅膀微微颤着,真像仙鹤展翅的模样。
鼓音不停,蝇虎子就不停变阵,进退转圜,丝毫不乱。有时两队“交战”,看似乱作一团,可鼓点一停,又能迅速归队,钻回竹管里,连一只掉队的都没有。曾叔政看得入了迷,直到王固塞好竹管,他才缓过神来,连声道:“先生这手艺,真是千古未见!”
第二天一早就,曾叔政急急忙忙去见于崸,把王固变成虎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。于崸这才惊觉自己看走了眼,拍着大腿后悔:“我竟把这般奇人给错过了!快,快派人去寻他!”
可派出去的人找遍了襄州的驿馆和客栈,都没见着王固的踪影——他头天晚上就收拾行李,悄悄离开了。于崸站在府门前,望着空荡荡的街道,心里又悔又叹:自己这辈子办过不少大事,却栽在“急躁”二字上,因一时的怠慢,错失了这样一位有真本事的人。
后来这事在襄州传了开来,有人说王固的蝇虎子是用秘术训练的,也有人说他懂鸟兽语言。可不管怎么说,大家都记住了一件事:别拿外表定高低,别用快慢论深浅。就像于崸,若当初多给王固一点耐心,或许就能亲眼见到那千古奇景;若我们待人时少些浮躁,多些尊重,说不定就能发现身边藏着的“高人”。
毕竟,真正的本事,从不在衣着是否光鲜,动作是否利落,而在那些不轻易显露的细节里——就像那不起眼的蝇虎子,也能在鼓点中,跳出最精妙的阵仗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5、符契元
唐穆宗长庆初年的长安,昊天观的符契元道长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他是福建人,不仅德行深厚,还通法术,观里的道士敬重他,连京城里的官员都常来请教,名气大得很。
这年仲夏的一个清晨,符道长把弟子们叫到跟前,叮嘱道:“我要静坐片刻,你们千万别来打扰。”说完便关上房门,在屋里躺下了。弟子们守在门外,不敢有半点动静,可屋里的符道长,却遇上了件奇事——四位道骨仙风的人找上门来,邀他出门游历。
符道长心里刚想着要去某处,身体竟真的飘了起来,跟着四人往外走。他离家三十多年,早就想回福建老家看看,念头刚起,脚就落在了故乡的土地上。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一沉:自家的老房子塌了半边,院墙倒在地上,园子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,当年认识的街坊邻居,没剩下几个。
院角的果树结着青果子,还没熟,几个邻家小孩正爬在树上摘,树枝被晃得直响。符道长看着心疼,忍不住呵斥:“果子还没熟,别糟蹋了!”可孩子们像没听见似的,照样摘得欢。他更生气了,正要上前阻拦,身边的道流却拉住他:“熟了的果子会被摘,没熟的早晚也会落,都是一样的归宿,何必放在心上?”
符道长愣了愣,想起自己早年在条山炼药的日子,又想再去看看那片山。刚这么一想,眼前的景色又变了——条山的青崖绿水就在眼前,山间的雾气沾在衣摆上,凉丝丝的。他跟着道流们走遍了当年去过的岩谷,看够了熟悉的风景,直到夕阳把云彩染成橘红色,道流才说:“天晚了,该回长安了。”
几人往回走,刚踏上京城的路,就听见远处传来马蹄声和吆喝声——是官员出行的仪仗,前呼后拥的,排场很大。符道长习惯性地想往路边躲,道流却笑着说:“阳间的官员,不必躲阴间的使者,你只管往前走。”
话音刚落,仪仗队里领头的几个人就看见了符道长,原本挺直的腰杆瞬间弯了,脸上的傲气也没了,慌慌张张地往旁边躲,连马都勒住了,生怕撞到他。符道长这才明白,身边的道流不是普通人,自己刚才的“游历”,也不是寻常的出门——是魂魄出窍,跟着阴间的使者走了一遭。
等他回到昊天观的屋里,睁开眼时,窗外的太阳还挂在半空,像是只眯了会儿。他把刚才的事告诉弟子,弟子们又惊又叹。后来有人说,符道长因为德行高,连阴间的使者都敬他三分,才会带他魂游故乡和旧地;也有人说,那“不必避阳官”的话,是在提醒他:心正行端的人,无论面对阳间的权贵还是阴间的规矩,都能坦坦荡荡。
符道长后来常跟人说,那次魂游让他懂了两件事:一是世间的得失起落,就像没熟的果子,强求不来,也不必耿耿于怀;二是做人做事,只要守住本心,行得正站得直,就不用怕任何权势。就像他站在官员仪仗前不躲闪,不是因为有法术,是因为心里没愧——这世上最硬的“靠山”,从来不是权势,而是自己的德行。
6、白皎
唐穆宗长庆年间,有个叫樊宗仁的读书人,在河阳节度使府做幕僚。这年他得了闲,想顺着长江游鄂渚,再去江陵拜访故人。出门时没多斟酌,就雇了个叫王升的船夫——谁料这王升看着老实,一上船就露了本性。
樊宗仁那时还在准备考进士,手无缚鸡之力,性子又温和。王升见他好欺负,便天天偷懒耍滑,不仅把船划得慢悠悠的,还总找借口要额外的钱。有时樊宗仁想喝口热汤,王升就摔摔打打地说“江里哪来的柴火”;夜里船停在岸边,王升还会偷偷拿他行李里的干粮去换酒喝。樊宗仁心里窝火,可一路荒江野渡,换船不易,只能忍着,每次都好言好语地迁就。
好不容易到了江陵,樊宗仁实在忍不下去,就把王升欺负他的事告诉了江陵府的官员——那官员是他同乡,听了很生气,当即派人把王升抓来,按律打了几十杖。王升被打得龇牙咧嘴,临走时盯着樊宗仁,眼神里满是怨毒,撂下一句“你等着”,就一瘸一拐地走了。樊宗仁没把这话放在心上,只当是他嘴硬,换了艘船,继续往三峡方向去。
可刚离开江陵没十天,怪事就来了。那天清晨,樊宗仁的船正顺着江水往下漂,突然之间,船缆像被什么东西割断似的,“啪”地断了。船夫慌忙去撑篙,可篙杆刚碰到水面,就像被无形的手攥住,怎么也动不了;想划橹,橹也卡在船舷里,纹丝不动。满船的人都慌了,船夫脸色煞白,哆哆嗦嗦地说:“这不是风大水急,是有人用邪术禁了咱们的船!昨天咱们是不是得罪谁了?照这情形,再往下走不到五百里,就是江里最险的石滩,那王升肯定是算计着咱们到那儿时,船就会撞碎沉底!”
樊宗仁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才想起王升临走时的狠话。他不敢耽搁,赶紧和仆人跳上岸,找了根粗麻绳,一头拴在船上,一头攥在手里,沿着江边慢慢往前走——船就像被牵着的牲口,在江里跟着岸边的人漂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第二天中午,果然到了那处石滩。只见江面上乱石林立,水流湍急,浪花拍在石头上,溅起好几丈高。刚到滩口,樊宗仁手里的麻绳突然被拽得紧紧的,江里的船像疯了似的,直往石头上撞,一会儿被浪掀得老高,一会儿又往下沉,船板“咯吱咯吱”响,像是随时要散架。没一会儿,船就真的碎了,木板和行李顺着江水漂走,多亏有麻绳拴着,船上的人才没掉进江里。
可麻烦还在后头。这三峡深处偏僻得很,上下几百里都没人烟,樊宗仁和仆人站在岸边,看着空荡荡的江面,又冷又饿,不知该往哪儿走。正发愁时,忽然听见林子里有动静,出来几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山獠——他们是当地的土着,靠打猎和采药为生。山獠见樊宗仁一行人狼狈,就主动递了些野果和干粮,问清了缘由。
一个年长的山獠听完,叹了口气说:“在三峡里用邪术害人的,可不止一个王升,好多船都栽过跟头。别人的邪术还好解,可要是王升做的,那是不把人淹死不罢休——你们这次怕是真遇上他了。不过咱们南山有个叫白皎的先生,法术通神,能破这种邪术,还能把施术的人召来。我知道白皎先生住在哪儿,我去帮你们请他来吧。”
樊宗仁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连忙作揖道谢。那山獠转身进了林子,第二天一早,就带着个道士回来了。这道士就是白皎,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道袍,头上戴顶旧黄冠,手里拄着根竹杖,脚上的草鞋沾着泥,看着就像个普通的山野村民,可眼睛却亮得很,透着股沉稳的劲儿。
樊宗仁赶紧把自己怎么被王升欺负、船怎么被禁、又怎么撞碎的事,一五一十地说了,语气里满是焦急。白皎听完,却笑了笑,摆了摆手说:“不过是件小事,你别急,我这就把王升召来,替你解决了他。”
说完,白皎就带着众人到了一块空地上。他让樊宗仁的仆人帮忙,割了些杂草,砍了几根细木,在地上圈出一块三尺见方的地方当法坛,又在法坛四周摆上几碗清水,插了几把刀,自己则站在法坛中央,闭上眼睛,开始默念咒语。
等到月亮升得老高,山里静悄悄的,只有溪水“叮咚”作响,杉树和桂树的影子在月光下朦朦胧胧。这时,白皎突然睁开眼,深吸一口气,朝着江面的方向喊了起来:“王升!速来!”他的声音清亮又悠长,顺着山谷传出去,老远都能听见。就这么喊了一夜,直到天快亮了,王升也没出现。
樊宗仁悄悄跟仆人嘀咕:“从江陵到这儿,少说也有七百里地,王升怎么可能说召来就召来?是不是白皎先生的法术不管用啊?”
这话刚好被白皎听见了。他转过头,看着樊宗仁,语气平静地说:“不是法术不管用,是这王升心里有鬼,躲着不敢来。不过他躲得了一时,躲不了一世——你且等着,我再用个法子,让他自投罗网。”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大奉后宫人 神女衔玉而生,三国大佬争疯了 穿越黄油后主动做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前文明牢舰的日常 战锤:从失落世界开始 火影交流万倍返还,我爽到极致! 99西游记 逆贼竟是我自己 以为只是虚拟游戏的我,被迫永远留在了这里 仙剑 在诸天万界成为臭名昭着怎么办 九阳圣体:开局绑定冰山师尊 偷窥系统?我观想万仙!证道成尊 绑架的千金小姐居然是个抖M贱婢,处女逼当场潮吹求开苞,跪舔绑匪鸡巴自愿当母狗,献金献逼怀野种 一指禅 不相爱就无法离开的房间 名侦探柯南的H游戏 啪啪代操 恩雅的堕落花嫁修业 和师父大人同修的第一百零八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