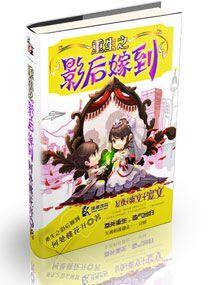630看书网>诗国行:粤语诗鉴赏集 > 第718章 粤韵凝魂昆仑铸魄(第1页)
第718章 粤韵凝魂昆仑铸魄(第1页)
《我哋嘅昆仑啊》(粤语诗)
文树科
巍巍昆仑山!
昆仑系山咩?
山海话丘墟
神集群绵绵……
佢喺新青藏?
佢喺乡下边?
滔滔黄河啊
滚滚长江水……
跟问万里墙
龙人心上城?
登高睇月近
茫茫原原线……
一盘冰心玉
昆仑光缘见……
《诗国行》(粤语诗鉴赏集)2025.9.19.藏区拉萨河畔
粤韵凝魂,昆仑铸魄
——树科《我哋嘅昆仑啊》诗学解构
文阿蛋
在汉语诗歌的长河中,方言诗歌始终以其独特的地域肌理与文化基因,成为映照民族精神光谱的重要支流。树科创作的粤语诗《我哋嘅昆仑啊》,以岭南方言为舟,载华夏山河之魂,在“巍巍昆仑”的意象建构中,完成了一次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文化对话。这首收录于《诗国行》(2025年9月19日藏区拉萨河畔藏版)的诗作,既保留了粤语诗歌的市井温度与韵律美感,又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中“昆仑”意象的厚重底蕴,其诗学价值不仅在于语言形式的创新,更在于通过方言与经典意象的碰撞,重构了现代人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认知与情感联结。
一、方言诗学:粤语的韵律张力与情感在场
粤语作为中古汉语的“活化石”,其九声六调的语音系统与丰富的虚词、语气词,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独特的韵律空间。《我哋嘅昆仑啊》开篇即以“巍巍昆仑山!昆仑系山咩?”的诘问破题,其中“系”(是)、“咩”(吗)等粤语常用虚词,不仅构建了口语化的对话语境,更通过语气词的韵律变化,赋予诗歌灵动的节奏感。相较于普通话诗歌的规整韵律,粤语诗歌的声韵体系更贴近古代汉语的语音特征,如“山”“墟”“绵”等字的押韵,既符合粤语中“殷”韵的发音规律,又暗合《诗经》“风、雅、颂”的声韵传统,形成“古今对话”的韵律张力。
从情感表达层面来看,粤语的方言特质让诗歌的情感传递更具“在场性”。诗中“佢喺新青藏?佢喺乡下边?”的设问,以“佢”(它)、“喺”(在)等方言代词与动词,构建了一种亲切的“对话视角”,仿佛诗人正站在山河之间,与昆仑进行一场私密的交谈。这种“在场感”的营造,打破了传统山水诗的“静观视角”,让读者得以通过方言的“烟火气”,感受到诗人对昆仑的真切叩问——既是对地理空间的追问,也是对文化认同的探寻。正如清代诗论家叶燮在《原诗》中所言:“诗之基,其人之胸襟是也。”树科以粤语为载体,将个人胸襟与山河气象融为一体,让方言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工具,而是成为情感与文化的“容器”,承载着对民族根脉的深情凝望。
此外,粤语中丰富的叠词与语气词,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情感浓度。“神集群绵绵”中的“绵绵”,既描绘出神山群峰连绵不绝的视觉景象,又通过粤语中叠词的轻柔发音,传递出对神灵的敬畏与温情;“茫茫原原线”中的“茫茫”“原原”,则以叠词的韵律感,勾勒出高原辽阔无垠的空间意境,让读者在语言的节奏中,感受到山河的雄浑与苍茫。这种“形神兼备”的语言表达,正是粤语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——它既保留了方言的“土味”,又兼具古典诗歌的“雅韵”,在“雅俗之间”找到了平衡。
二、意象解构:昆仑的多重文化意蕴与现代转译
“昆仑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,自《山海经》始,便承载着“神山”“河源”“天帝之都”等多重文化内涵。树科在《我哋嘅昆仑啊》中,并未简单复刻传统昆仑意象,而是通过方言的视角,对其进行现代性转译,让这一古老意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诗开篇“巍巍昆仑山!昆仑系山咩?”的诘问,看似简单的“是山与否”的追问,实则蕴含着对昆仑意象多重内涵的解构——昆仑究竟是地理意义上的山脉,还是文化意义上的精神符号?这种追问,为全诗的意象建构奠定了“虚实相生”的基调。
从地理意象层面来看,诗中“佢喺新青藏?佢喺乡下边?”的设问,直指昆仑的地理坐标。昆仑山横贯新疆、西藏、青海等地,是青藏高原的重要山脉,诗中“新青藏”的表述,既点明了昆仑的现代地理归属,又通过“乡下边”的方言表述,赋予其亲切的“家园感”。这种“宏大地理”与“微观家园”的并置,打破了传统昆仑意象的“神性距离”,让其从“天帝之都”的虚幻想象,回归到“家园山脉”的现实认知。正如《山海经?西山经》所载:“昆仑之丘,是实惟帝之下都。”传统昆仑是“帝之下都”的神圣空间,而树科则通过“乡下边”的方言表述,将其转化为“吾乡之山”的亲切存在,这种转化不仅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,更体现了现代人对“家园”的重新定义——山河不再是遥远的景观,而是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文化根脉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从文化意象层面来看,诗中“滔滔黄河啊,滚滚长江水……跟问万里墙,龙人心上城?”的诗句,将昆仑与黄河、长江、长城等核心文化符号并置,构建了一个完整的“中华文化意象群”。昆仑作为黄河、长江的发源地,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“河源之山”,诗中以“滔滔黄河”“滚滚长江”呼应昆仑,既符合地理事实,又暗合“饮水思源”的文化传统。而“万里墙”(长城)与“龙人心上城”的关联,则将昆仑的意象从“自然山脉”延伸至“精神长城”——昆仑不仅是地理上的屏障,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“心城”,是“龙人”(中国人)的文化认同所在。这种意象的拓展,让昆仑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,既承载着“山河之魂”,又凝聚着“民族之魄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,诗中“一盘冰心玉,昆仑光缘见”的诗句,对昆仑意象进行了“灵性化”的升华。“冰心玉”既呼应了昆仑“产玉之山”的传统认知(《山海经》载昆仑“有玉膏,其源沸沸汤汤”),又化用了王昌龄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诗句,赋予昆仑以“高洁之魂”。而“光缘见”的表述,则以“光”为媒介,将昆仑的“神性”与“人性”连接起来——昆仑的光芒,只有心怀“冰心”之人才能看见,这既是对“知音”文化的传承,也是对现代人精神境界的期许。正如南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?神思》中所言: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树科在诗中所展现的,正是这种“情与景偕,意与象通”的诗学境界,让昆仑意象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,焕发出新的精神光芒。
三、文化认同:方言与经典的对话,个体与民族的联结
在全球化语境下,方言诗歌的创作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创新,更是文化认同的重构。《我哋嘅昆仑啊》以粤语为载体,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、边疆文化连接起来,在“方言—经典—民族”的三重维度中,构建了完整的文化认同体系。诗中“我哋”(我们)的称谓,看似简单的方言代词,实则蕴含着强烈的“共同体意识”——“我哋嘅昆仑”不仅是诗人个人心中的昆仑,更是“我们”(中华民族)共同的昆仑,这种称谓的选择,让诗歌的情感表达从“个人”上升到“民族”,完成了个体情感与民族情感的联结。
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话来看,粤语作为岭南文化的核心载体,其与中原文化的交融由来已久。树科在诗中以粤语书写昆仑,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体现——岭南的“方言之韵”与中原的“山河之魂”相互碰撞,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。诗中“登高睇月近”的诗句,既化用了王维“明月松间照”的古典意境,又以粤语“睇”(看)的口语化表达,赋予其岭南文化的“市井气息”,让古典诗意与方言韵味完美融合。这种融合,打破了地域文化的界限,证明了方言不仅是地域文化的“载体”,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“见证”。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:“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。”《我哋嘅昆仑啊》所展现的,正是这种“美美与共”的文化境界——岭南文化的“美”与中原文化的“美”相互映衬,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“大同”。
从个体与民族的联结来看,诗歌中的“登高”意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。“登高睇月近,茫茫原原线”,诗人通过“登高”的动作,既实现了空间上的“视野拓展”,从岭南的“乡下边”望向青藏的“昆仑山”,又完成了精神上的“境界提升”,从个体的“小我”走向民族的“大我”。这种“登高”意象,与杜甫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精神一脉相承,都是通过“登高”来实现个体与山河、民族的联结。而诗中的“月”意象,更是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文化符号——无论是岭南的“月”,还是青藏的“月”,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“明月”,这种意象的选择,进一步强化了“民族共同体”的意识。
此外,诗的创作背景——2025年9月19日藏区拉萨河畔,也为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“空间语境”。拉萨河畔作为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,与岭南文化、中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。诗人在藏区书写昆仑,既是对边疆文化的致敬,也是对“多元一体”中华民族文化格局的认同。诗中“昆仑光缘见”的“光”,不仅是昆仑的自然之光,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“精神之光”——这种光芒,照亮了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,让“我哋”(我们)在共同的文化根脉中,实现了精神的凝聚与认同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四、诗学价值:方言诗歌的现代性探索与文化传承
《我哋嘅昆仑啊》的诗学价值,不仅在于其优秀的文本质量,更在于它为方言诗歌的现代性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。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中,方言诗歌曾一度处于“边缘地位”,被视为“小众”“土味”的代表。而树科的这首诗作,通过“方言+经典意象”的创作模式,证明了方言诗歌不仅可以具有“雅韵”,更可以承载厚重的文化内涵,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从语言形式的创新来看,这首诗打破了“方言诗歌=口语化”的刻板印象,实现了“方言的雅化”。诗中既运用了“系”“咩”“佢”等口语化的方言词汇,又化用了《山海经》《诗经》等经典文献的意象与句式,让方言与经典在语言层面实现了“对话”。这种“对话”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层次,更让方言从“民间语言”上升到“文学语言”的高度,拓展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边界。正如现代诗论家朱自清在《新诗杂话》中所言:“新诗的语言得是活的语言,得是日常口语的提炼。”树科的这首诗,正是对“活的语言”的最好诠释——它既保留了日常口语的“鲜活”,又经过了文学的“提炼”,让方言成为既“接地气”又“有底蕴”的诗歌语言。
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,这首诗为“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”提供了重要的范例。昆仑、黄河、长江、长城等传统意象,在诗中不再是“博物馆式”的静态展示,而是通过方言的视角,被赋予了现代的情感与认知。诗中“昆仑系山咩?”的诘问,正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“重新叩问”——我们如何理解传统?如何在现代语境中传承传统?树科给出的答案是:以方言为“桥梁”,让传统意象与现代情感相连,让传统文化“活”在当下。这种传承方式,既避免了“复古主义”的僵化,又避免了“西化主义”的无根,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开辟了新的路径。
此外,这首诗还展现了“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”的共生关系。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方言、民俗、审美观念等,都具有独特的价值。《我哋嘅昆仑啊》以岭南方言书写中华民族的核心意象——昆仑,正是“地域文化融入民族文化”的生动体现。这种融入,不是“地域文化的消亡”,而是“地域文化的升华”——岭南文化通过与民族文化的融合,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;而民族文化也通过吸收地域文化的精华,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元。这种“共生关系”的展现,为中华民族文化的“多元一体”格局,提供了诗性的证明。
结语:
树科的《我哋嘅昆仑啊》,是一首“有温度、有厚度、有深度”的方言诗作。它以粤语为韵律之舟,载昆仑之魂、山河之魄,在语言的河流中,完成了一次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文化航行。诗中既有“巍巍昆仑”的雄浑气象,又有“系山咩”的亲切诘问;既有《山海经》的古老底蕴,又有现代的情感叩问。在这首诗中,方言不再是“小众”的语言,而是成为连接个体与民族、传统与现代的“精神纽带”;昆仑也不再是遥远的神山,而是成为“我哋”(我们)共同的文化根脉。
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,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。《我哋嘅昆仑啊》告诉我们:文化的传承不是僵化的复制,而是活态的创新;民族的认同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具体的情感。当我们以方言为视角,重新审视昆仑、黄河、长江这些共同的文化符号时,我们会发现,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,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个“我哋”的心中,在方言的韵律里,在山河的意象中,在共同的精神凝望里,生生不息,代代相传。
喜欢诗国行:粤语诗鉴赏集请大家收藏:()诗国行:粤语诗鉴赏集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七零咸鱼继母的养娃日常 法老的宠妃1 法老的宠妃2 穿越之我家有男媳 重生为康熙的小青梅躺平一生(清穿) 法老的宠妃3终结篇 她谋 11处特工皇妃(特工皇妃楚乔传) 末世捡到前妻后 万人迷[快穿] 用柯学的方式阻止发刀 开局开出蛊罐,叮,开出无线寿命 深眠 阴湿男鬼觊觎的脸盲美人 阴鸷男主成了我寡嫂 在电竞文里又封神了 社恐雄虫被强制匹配后[虫族] 太子的外室美人 嫁给一个老皇帝 造反大师